 |
|
 |
|
季先生的生命之树蔓生出一些遗憾的枝丫,生前萌发的,身后并没有停止生长……

图| 季羡林先生
01
怀念朗润园可以自由进出季羡林先生家的时光。20世纪80年代,年过七旬的季先生每日缺月尚在即起,安安静静在这栋普通民居的一楼面对当时最普通的防盗窗用功,从头发有些花白到全白,越来越稀疏。每次到楼下我先站在窗前看这仙人球般的宽阔头顶,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也看不到我,打扰不到他,我可以安心地多站一会儿。
我不会去敲门,而是拐入旁边的单元,径直上三楼,先去看金克木先生。矮小的金先生穿着和季先生一模一样的旧中山装,生动活跃过于季先生十倍。不会冷场甚至插不上嘴的“谈话”会持续很久,轻松高兴仗着是晚辈又仗着熟悉无拘无束地提问、抢话,在不拘小节的房间里东走西看,哪怕被金先生问得张口结舌也毫不尴尬,顺风顺水地引出更多的话题。金先生有意无意地每次都会问一句:“去过那边了吧?”也并不想得到回答。那边,就是季先生家。我每次都会诚实地告诉他,一会儿就去。
在季先生家,我不由自主地老实安静下来。季先生话少,安静地坐着,诚恳地看着你,好像在等待着分配给他的任务。但话再少,也每次都会问一句:“是从那边过来吗?”我诚实地告诉他,是的。我告诉季先生,金先生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他说他的脑子不好,腿不行,眼睛不好,耳朵不灵,牙也坏了,头晕血压高,将不久于人世了。季先生浅笑说,二十年前他就这样说了。
季先生、金先生同住在北大朗润园13号楼,分住在两个单元的一楼和三楼,同在北大东语系,同是梵文和印度学专家,不同的是,早年只有小学学历的金克木先生赴印度鹿野苑梵都苦修,清华大学毕业的季先生则作为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赴德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图| 季先生在德国哥廷根
两位先生殊途同归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东语系,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好像季先生没写过金先生,金先生也没有文字评价过季先生。他们在同一学府以各自不同的方法授业解惑,金先生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季先生引经据典,系统周详。所谓各有千秋,都得到了学生的好评和敬仰。他们和与他们同时代的一些知名学者构成了当代的学界风景,文坛风景,丰富多姿。看到陈丹青画笔下“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先贤,赵元任的西装领带皮鞋,王国维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并为一列。真可惜这种风景我们没能见到,但季先生、金先生,还有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还有吴组缃、邓广铭、王瑶、季镇淮……我是有幸亲见的。但可惜这种风景也没有了。

图| 朗润园住宅区,季羡林先生生前住在这里
季先生出生毕竟晚于国学研究院的五位老先生几年,他可能只有过赵元任先生的西装装扮,长袍马褂我们没有见过,但见过先生戴过形同瓜皮帽的睡帽。季先生和上面诸位先生的服装似乎是统一的年代工作装:中山装。
2000年之后接触季先生逐渐逐渐少了,敬中逐渐逐渐加入了一些畏,不是季先生可畏,而是他的周围逐渐逐渐被包裹上了一层保护膜,愈来愈厚。最后几年住在301医院,有几次机会去看他,想想还是没有去。似乎那时的探望成了一种膜拜,能去的人事后写文章要从进医院前的激动心情写起,然后是病房中的一物一景,季先生的须眉颦笑,对话中的一字一句。时令年节领导人会去探望。这成了一种象征。这些和季先生无关,季先生的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环绕在山水周围的整体环境有些变了。我只能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季先生,但也很满足。
02
2007年初季先生的《病榻杂记》出版,从这本书里,我了解到了季先生几次生病住院的过程,知道了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也慰藉了我几年来虽未去探望,但心中无尽的惦念。看到书中的季先生“现在正从炼狱里走出来,想重振雄风了”,真为先生能有这样的心境感到高兴。但我终究还是个悲观主义者,暗自感觉到季先生再回到朗润园的可能性很小了。
记得在《病榻杂记》出版座谈会上,我发言的最后一句话是“真心地盼望季先生能再回到朗润园,哪怕在‘季荷’塘边的椅子上再坐一坐也好!”那时我的心如被池塘的水浸过一样冰凉。我甚至想说在季先生的有生之年我怕是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他了。但终究和会场的气氛不符,也不合习俗,没有说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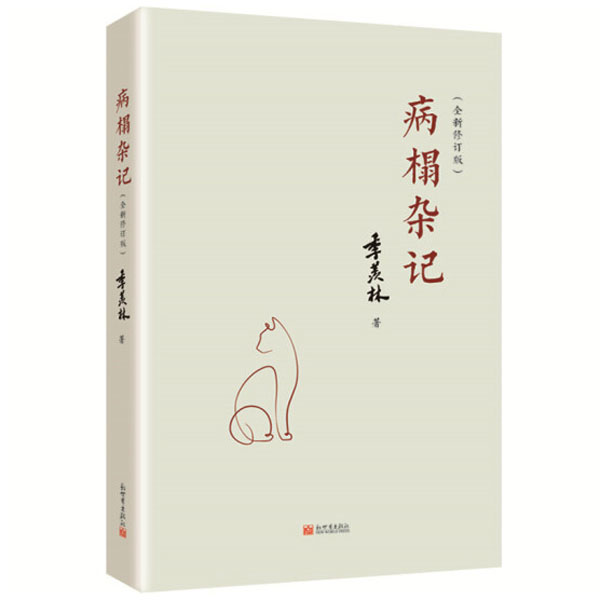
在这本书中又看到了“稚珊命题作文,我应命试作”,自责同时又很温暖。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约季先生写稿,无论是电话还是书面,印象中季先生从没有回绝和延误过,季先生以他特有的沉静寡语认真“遵命”,使我从没有因为他是名人而有过畏难情绪,约稿信提笔就写,电话说打就打,言辞间冬安春祺,敬语礼数是否周全好像都没有过多考虑。
季先生从不挑剔,总是按约定时间将写在“季羡林稿纸”上的文章寄到编辑部。新千年之初,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稚珊来信,要我写一篇关于世纪转换的文章。这样的要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已经接到过不知多少次了,电台、报纸、杂志等等,都曾对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我都一一谢绝了……但是,稚珊的要求我没加考虑就立即应允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因为我所供职的杂志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他有一份社会责任。同时如他所说,还有多年的友谊。不单是写稿,当时杂志社每月都要召开一次专题座谈会,约七八位专家学者,就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治、科技等领域政府关心、群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座谈。多次邀请季先生参加,他从不推辞。有两次他已因病告假,但在会议即将开始时他却赶了来,带给我们不小的惊喜。
记得有一次在季先生家,我有点玩笑地对季先生说:“季先生,别人认为向您约稿很难,对我却一直是有求必应,他们羡慕我,我也特有成就感。谢谢您!”季先生笑得很开心,幽默地说:“我是荣幸之至。”
03
和金克木先生一样,季先生内心也有一片菁菁芳草,相信到晚年仍旧是芳草萋萋。十八岁时,由抚养他长大的叔叔主持,孝子季羡林遵从母意,娶了大自己四岁、只读过小学的彭德华为妻,家长们执意要他孕育出一双儿女才允许他离家,儿子三个月大,他毅然别家,这一走就是留德十年、离家数十年,有给母亲报平安中规中矩的家书,却没有给妻子思念缠绵的私信。

图| 季先生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照
功成名就,在北大有过三代同堂的和睦之家,夫妻相敬如宾不同室,我每次去,总看到季先生的夫人和婶母同室对坐或操持家务,从不作声响,也不与客人攀谈。几次到午时,看到餐食也没有因季先生吃过十年洋面包而改变,总是绿豆小米粥、花生米、红薯等清素的家乡底味,一如这个过于安静的家庭一样清白寡欲。
季先生在德国留学时,也曾遇到一位品貌俱佳情投意合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那时的季先生挺拔温润清雅,穿着合体的风衣眼角眉梢总有笑意。共同的课业,耳鬓厮磨的探讨互助,他们心心相印。应姑娘之邀,在课余时间他们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有说不完的话,每次分手都是依依不舍。季先生终生没有对第二个女人有过这样的情感。
但季先生还是为了家庭的责任悄然离别了泪水长流挽留他的姑娘,书信也断绝了。1983年,季先生因公访问德国,叩响了三十年前熟悉的那扇门。遗憾的是故人不再,音讯杳然。季先生90岁生日,收到了伊姆加德的照片和信,她终生未嫁,一直守着为季先生打过论文的老式打字机,那是他们相识的媒介。

图| 伊姆加德
新观念旧礼教,新思维旧传统,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也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去衡量。但季先生沉默寡言、隐忍内敛的性格应该和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不无关系。季先生对老妻寡婶终身敬奉。
04
《清华园日记》是季先生就读清华时1932年至1934年的日记,也许对研究季先生的学者相当有用,我看过却从中认识了另一个季先生。
季先生托人将日记送到我手上时,他已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书的扉页题赠时间是2002年12月10日,我几乎是将近三年后才收到。这期间季先生和我可能都以为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的。可是没有,我再也没有见过有求必应的季先生。
我原以为季先生在清华园的日记一定是偏于学业和学术的,因为我们接触和读到的季先生是他的中晚年,中规中矩,有板有眼,不多说少道,三缄其口,谨言慎行,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楷模。挺意外的是季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
“妈的,真讨厌,大风呼呼地直刮了一天。”(1934年月19日)
“过午在张明哲屋打扑克,消磨了一下午。无论如何时间消磨了,总是痛快事。”(1934年1月21日)
“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1934年3月16日)
是季先生吗?是啊,是一个年轻的、有着正常的生命活力的、不加修饰的七十多年前的季先生。
怕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日后的七八十年他会与此完全隔绝了,人间烟火,本能欲求,甚至在中年就断绝了,成就了一位苦行的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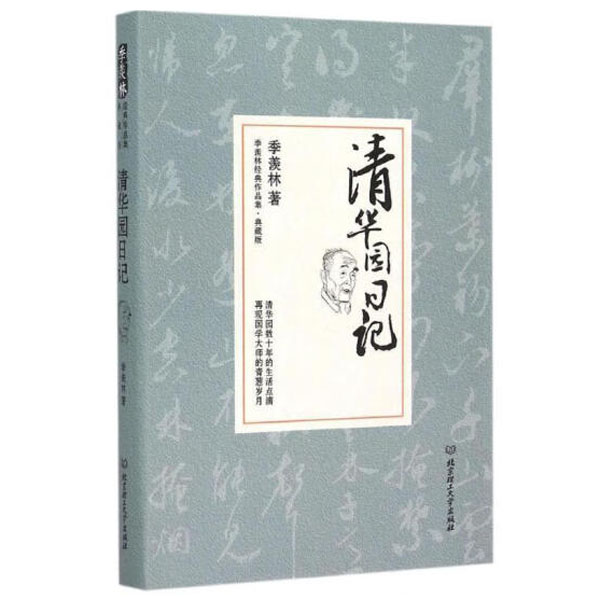
一个有常人般青葱岁月意气用事的学子,真情流露本也是寻常事,不寻常的是到了2002年,一个已经被众人仰视的学界楷模,能不悔、不避、不改少作,将这本日记公开出版。
季先生在后记中写道:“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在人前难以说出口的话,都写了进去。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把日记公开。有些话是不是要删掉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是圣人……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可惜,离开清华后的季先生再没有这样的口无遮拦。
时代、环境、际遇……一直不想当圣人的季先生 ,晚年身不由己,不虞之誉纷至沓来,他无法控制。光环不是自己加的,自己想摘也并不容易,他老人家的“三辞”非但没有使自己清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我相信老人是有心语要吐露的,只是惯于克己至深,再没有就此事多说。

图| 季羡林先生和猫
季先生还写过一篇散文《我有一个温馨的家》,也是我命题,至今想来后悔不已。文章写于2000年底,先是回忆了婶母、老伴和母亲,又用相当的篇幅写猫。“60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把这样一个家庭称之为温馨不正是恰如其分吗?”文章还几次自问:“这难道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吗?”
语言之外,文字之后,孤身生活的季先生的克制、回避,以及我们后来才知道的隐痛丝丝缕缕流露出来。我真不应该给季先生这样的命题,他也完全可以不写的。
过分的隐忍也许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季先生的生命之树蔓生出一些遗憾的枝丫,生前萌发的,身后并没有停止生长,我总是很心痛地想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人,能总是坐在季先生身旁,深得季先生信任,使他愿意把心中的淤积无保留地倾诉,让他的心能轻松敞亮些。也许有这样的人,也许季先生倾诉过,而为了季先生的灵魂能得以安息,没有人讲出来,我们都不会知道……
季先生走了十几年了,愿他的身心都得到安宁。(叶稚珊)
新民报系成员|客户端|官方微博|微信矩阵|新民网|广告刊例|战略合作伙伴
北大方正|上海音乐厅|中卫普信|今日头条|钱报网|中国网信网|中国禁毒网|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沪B2-20110022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3|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909381
广电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沪)字第536号|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5900430043|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044号|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590号|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57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044号|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590号|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579号
新民晚报官方网站 xinmin.cn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